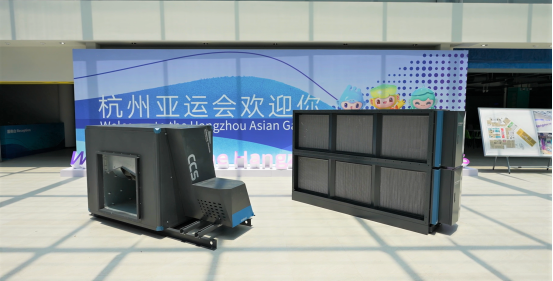异质与原念的无奈及守望
——也谈陈开平小说《白鲜肉》之三部曲
文¨尤青云

其实,人们在谈论陈开平的小说《白鲜肉》时大多关注的是主人公的命运和情节的特殊性,远一点关注的是其笔墨语言和内在的格局图形(文章也有无意识的意向图形),忽略了其文章的精神诉求。
多年前,我最早阅读陈开平先生的文章是从其散文开始的,在陈氏散文里“描写性语言”往往包含许多“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因此构成了作品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以“期待的视界”发挥想象力去进行再创造,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互动能量。事实上,这一行举在艺术家与读者、观者、感者的召唤之间是很有穿透力且难能可贵的,这需要有独特的语境风格、浓厚的生活体验、哲理思想及扇面性的深邃思维方可完成的行为动态,递进了艺术发展的思潮与思索空间感,似乎与严谨、格式、讲求的程式化所不敢苟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里尔克诗选》(绿原译)里,一向以深邃莫测、聚讼纷纭而又驰名遐迩的国际诗人赖纳·玛利亚.里尔克(Reiner Maria Rilke)竟有很多这方面的语境;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也同样有着“意义空白”与“召唤结构”,这也许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招牌愿景。就语言风格来说,陈开平的小说依然含有他的散文式的“召唤结构”,对文字驾驭似乎有其“天然的换新”意思,即能从生活中走进去又能走出来,从容自如地“出入”。之前著名作家、评论家杨府先生在以《独特的文学理想:探究人性与自然的关系——浅说陈开平中篇小说集<白鲜肉>的文学探索》为题时这样认为:
“他用那颇具诗化和象征意义化的创作手法和技巧,来处理社会现实问题并探讨生命的意义,这种探索很有意义。在作者笔下,每一个场景都是如此真实和动人心魄。在这些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意味:对语言形式进行颠覆、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也成为了陈开平小说创作最重要特征之一......”

评论者和读者都在从自体身上的感应迸发出来对《白鲜肉》的吉光片羽和不递。
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所谓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总有一种傲视和坚守人性物体的原念来吸引读者与之共鸣!最终之源泉来源于他们总有那些无与伦比的坚实生活的底子和原物性的人文情怀,这种元素一旦作家赋予“顶戴花翎”有可能会淡然失色。正因如此,当作者的作品里需要出现人、物命运的“异质”原物时,后现代主义作者如同没有成熟的孩子是无尚无奈和苦痛的,无奈和苦痛的来源是因为他们把所塑造的人物原念埋的太深,埋的愈深愈难发掘、愈难突破,以至于迸发出来需要的能量愈大,外表看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情到深处不言情”的真实体验,最后形成了极为强悍的穿透力。作为认真的读者,我深深地感知到作者在迷惑的灯光里站在窗台下的影子,面对如此,也许他(她)曾在那里哭泣过,以至于我在与陈君交谈的时候他不加掩面的告诉我,的确如此,就在写《白鲜肉》三部曲时的每一部作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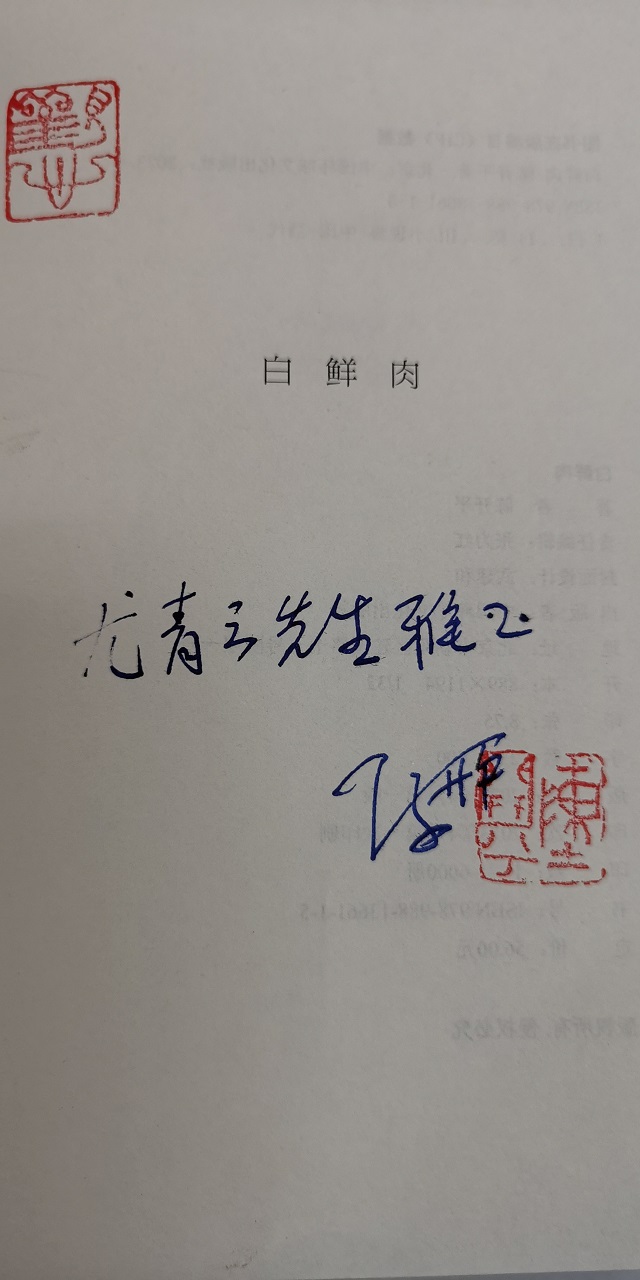
《白鲜肉》三部曲分别为《白打地》、《木履》、《那村叶儿六月黄》三篇,几乎所有读者都在问陈开平为什么将这个作品叫《白鲜肉》?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叫《白鲜肉》呢?”陈开平说:“我感到‘白鲜肉’最能体现书中主人公的原始气息和人性感召,再没有发现以此更为贴切的了,纵使《那村叶儿六月黄》的主人翁也是这个名字;也有些出版社有不同的建议,甚至于为此解除了合作,但我还是坚持这个想法......诚然,让其叫‘红鲜肉’、‘花鲜肉’也会有人发问的!”
陈开平还是认为“《白鲜肉》能体现书中主人公的原始气息和人性感召!”
《白鲜肉》全篇二十三万四千五百八十四个字,被三个中篇小说组成着,第一篇《白打地》,《白打地》的序言上就其本人说:创作源泉来源于一场在都市夜晚的梦境:少年时代的白云;记忆里较为“年轻”近六十岁的爹、娘;这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在那个时代定会隐藏着较为深厚的故事等等,无疑给就了读者一个干净、甜然、厚重的空间想象,全篇文章分为七章,每一章的标题用的是词牌名,增添了文章的悠远气息和典朴味道,故事情节大体分为:父亲“官二哥”在蓝县跟人做生意时银元的“丢失”;用弹弓射伤自称是曹操后代呆三的阴部;与母亲满堂春的恋情,满堂春的小脚与脚下刺绣的玫瑰花及染红了的脚趾甲;“官二哥”被歹人抢掠后,满堂春在三省庄救夫;“官二哥”、满堂春跳到花打地河里自尽等为主线。
《木履》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处骨脊山山脉玉山角下的陈楼村的故事。这一年天奇旱,雕刻木履的能手——“鬼手”之子柳怀仁的小老婆红杏符合求雨的条件,红杏生来美丽、甜蜜、小巧玲珑,长着一双青桃一样的眼睛。在柳怀仁的劝说下红杏接受了难以唇耻求雨行举,求雨仪式极为隆重,柳怀仁把赤身裸体的红杏背回了家,在回家的路上二人“演绎”出来了红杏坎坷不幸的一生,小说故事跌宕起伏,构思奇巧、新颖别致,富有凄楚之美。
《那村叶儿六月黄》以两头忙河为背景,描写了陈楼村与烟袋头村之间发生的人文情怀:烟袋头村的白家小姐白鲜肉“韵味十足,尤其是那个乳房,如同他娘的乳房一样丰韵,仿佛就是从娘身上移植下来的又长到她的身上,里面蕴藏着兜不住的风情,如同蜜桃一样传送着丰富而神秘”(——出自《那村叶儿六月黄》)的故事。白鲜肉嫁给陈家在外边求学的公子陈青蓝,陈家公子青蓝与小姐陈蓝堡二人长期在外上学接受了新的思想,年事以高的陈氏父亲陈文卿是读书人,对于名声和村庄、村族的守望立于纸背,同样渴望追求远方的陈氏主人与其振兴家乡的心灵愿景而需求的人力资源青黄不接!新来的“灵动得像两头忙河的水一样让人迷惑,手指细长白嫩,让人看着眼馋。温情灵动的眼神中似乎埋藏着娘的隐忍及爹的浮华和任性的白鲜肉。”(——出自《那村叶儿六月黄》)肩负重担,变成了“花木兰”,当然,花木兰(蓝)本是豆科木蓝属的小灌木植物,花序均疏生白色纤小,鲜花会因之以天然之美被风雨戏弄......
三个小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既有深刻思考又充满温情,既呼唤人性又遵从自然。主线都是围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以作者家族及其名叫“陈楼村”里的事件为背景,以满堂春、红杏、白鲜肉三位女性为描述对象。如果把女性比大地的话,陈开平似乎擅于描写女性的纯美及她们的内心世界,因许当初其家庭受政治的影响,因而他幼、少时代身心对爱的缺失,因之缺少所以想象。
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终极寻找的是自己、寻找自己失去的!艺术同样如此,作家的寻找最终是心灵当中的自己!当心灵的本物被生活亦或事俗打败时体验的毕竟是悲剧色彩!当“东边圆滚滚的月亮升起来了,像一张皮影照在圆圆的白纸上,白得发黑,黝黑温润得能吸出水来,挂在嫩桃家的干草垛上,用竹竿一戳就能戳下来拿回家去。”时(——出自《木履》),注定“红杏像一只伤痕累累久未闻蝉的征雁在“打斗”中败下阵来,飞跑了。盐粒一样的雪打在她的脸上如同成熟于夏季的麦子锋芒。”(——出自《木履》),她(它)太美了!美会伤身的!无以奈何又何奈何!?有时候生活是个即“闪亮”又“诱人”的恶魔,为什么如此惨烈?
也许作家的题材都是伪命题,也许有他的影子哪怕是期望!
陈开平在一次创作谈《<白鲜肉>在我心中》说过:“当我完成《白打地》的时候我还是认为似乎该说的话还是没有说完,有必要再说下去,让它成为一个系列出来展示于人们,紧接着就写了《木履》、《那村叶儿六月黄》。现在想来,世间慢长的岁月自然给了我无尽的思考和想象。”他认为他该说的话没有说完。
有时候我想:只有经受过生活的炙烤感受过疼痛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美与丽的感想与感受,才能产生揭开伤口的勇气,揭开伤口与回味疼痛以此来以警其身,不会再发生了吧!那个“好”在他(她)心里!在他(她)的自然之间的空间意思和想象力里,纵使“过尽千帆皆不是”。实则从他之前笔下的《一天》、《那边》、《磨坊》、《小河》、《远山》、《白云一去又几年》等作品里也可以体会到陈开平是个善于通过自然构成与人物形象乃至于人物内心世界用文字互惠照应的作家,只是换了个汤,药没有换而已,难怪评论家“风生水起”在看了陈氏作品后如是说:现在看来作家真不是培训产生的,“培训只是可以唤醒人的禀赋和灵性,很多天资纵横的人,即使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培训,也最终歪歪扭扭地走到路上来,而且一但上路就灵性勃发,陈开平就属于这种人,对于文字有天生的灵感和驾驶力,会很精确地用文字表达极其细微的感觉甚至是潜意识。”
《白打地》里对自然与自然形成的个体之间的描写上有这样两段话:
“失去了往日的风流韵事,下年的槐花在催促着它们慢慢得老去。花打地两岸的豌豆花接踵而来,大自然像一个不断变化菜谱的宴席,你方唱罢我登场”;“蛙声慵倦地叫着,天边悠荡着淡绿色的浮云,苍茫淡远,细如游丝,飘飘荡荡觅寻处,纠缠如兔丝附于蓬麻”;“满堂春像一朵娇嫩被风霜打过的鲜花,带着被明矾与凤仙花染指过的风韵和芬芳,眼睫毛挂着闪烁的泪滴,两只鼓鼓的乳房如同挣扎着的白色兔子”。
显而易见,人的形象思维需要有生活的,生活要与自然接轨,与自然产生呼应,无法弄虚作假!我之所以在此反反复复地谈到自然与人的关系,因为自然是物质世界!你我是人!“的的确确文字语言是个饥饿的馋鬼,它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要有厚积薄发的知识储藏”,万念以蕃息畜藏,需求人与自然的反刍意思;“然后,无论你运用怎样的形式,都要将缠绕一团的感觉雾露理清、符码化,成行为读者认可的有创造性意味的文字,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元气充盈!”生活的打磨。诚然,再优秀的作家创作都是有条件的,纵使陈开平说过:“作家你必须会创作,是生活的造就者,而不是只会纪实身边的故事!”。身为农人的陈开平在一次《白鲜肉》作品研讨会上说:“也许我的一生都是在晚中度过的,父母生我时已经四十大多了这是一晚,三十三岁那年才离开农村二晚,少年习作近六十岁出版一本书三晚,四十余岁来到都市四晚也......”《晚熟的人》似乎成为陈开平的一个符号,是的!人生总会给艺术家无情地开玩笑,先让他(她)狠狠地跌倒,让其俯视大地一翻,他们再没有时间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曾经的名利具过往也!
“人的成熟正如橘子一样,必须有春天花蕾的绽放、夏天火的炙烤,才有秋的红晕。”——出自《白打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开平出生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农村家庭,有过坎坷的经历和不同寻常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于壮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经历了很多次的政治、集体、产业、人事等当中的大变革,家境在政治上的磨难让陈开平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目睹、经受了家庭和本人被欺凌的深痛,父亲期望其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求,渴望“曙光”(陈开平的乳名后为笔名)再照!家庭希望的寄托使其散发出无比的想象,可是生活最终把他打落尘埃;兄、姊间的年龄结构;婚姻的不幸......很多的时候成了无物之阵,迷惑、迷茫、期盼、遐想、神韵、空灵在他的脑海里像个皮影,少年时代它曾经仰卧在小河边看白云变化很久而不归;由于学生在校欺凌他爬到树杈上躲起来不愿意上学;躲在麦地里不敢回家......“在历史的裂变中,普通人的命运是不由自我掌控的,每个人只有去守望剩余的自我以及无奈地接受自己那被权威塑造成的摸样。‘自由’是被施舍的,反抗只会造成无情的打压。”他只有从自然中寻找!那里有他的精神原乡!即使它不被存在!读者在他的《空中学校》里或许找到一点他当时的影子。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后,失落和迷惘中突围成就了勇者特别是作家的精神症结和力的滋生,更是他们超越自我、拯救自我的精神毓丽。即使“世间的万物总归为尘土。”——出自《那村叶儿六月黄》
陈开平在创作谈《<白鲜肉>在我心中》时这样写到:“我为了一段自然的描写甚至于夜晚出去观察月亮很久很久,月亮的光影穿过树叶的样子,默默地看朋友似笑非笑时脸上所荡漾的表情而还不能让对方发现。”“两只驴远远地看到了两头忙桥,欢叫了一声在两头忙桥上立住了,八条腿在地上相互倒腾着,太阳如‘胖驴’的肚子一样鼓鼓地从地上冒。”——出自《那村叶儿六月黄》,这是怎样的思维和语境!
任何作家都有争鸣,也要有争鸣,只有争鸣才有更好的摄取。《白鲜肉》有其扑街之处,我认为陈氏作品过之追求语言的境界与语境的超越性而失去了他原本需要的严密性,我坚信作者自己应该能发现,这丝毫不会影响其作品的生命力。因为大作家必有创而作之的情怀与胆量!

诚然,没有人天生就是作家。当情绪淹没了城市精神人的疲惫和厌倦时,人们总要回望原乡,再来当一次《原乡人》,故乡的原野会接住了他!把“纸上”的人和事成为风景,来一番《白鲜肉》样的精神图腾。
二0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晨修改于北京
作者【陈开平:中国当代作家,文艺评论家,北大《华商评论》主笔;详见:百度百科、中国作家官网、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零时古怪 - 中国第一时事资讯综合门户 » 异质与原念的无奈及守望——也谈陈开平小说《白鲜肉》之三部曲
 零时古怪 - 中国第一时事资讯综合门户
零时古怪 - 中国第一时事资讯综合门户